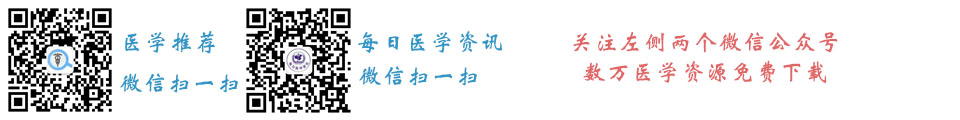图示:艾滋病研究人员乐观地认为,他们离艾滋病疫苗越来越近了。
自发现艾滋病毒三十五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开发艾滋病疫苗。而有人认为,现有的研究范式使得疫苗研究的方向错了。相比之下,经典疫苗学反而更有可能击败艾滋病毒。
据国外媒体报道,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伯特? 多尔曼 (Burt Dorman) 准备退出疫苗接种领域。作为一名生物物理化学家,他花了数年时间成功经营一家制造动物疫苗的公司。这家公司开发出十几种针对猫科动物白血病和水疱性口炎等疾病的疫苗。随后多尔曼在一个新领域开创了一家致力于疾病诊断的新公司,致力于疾病诊断。
然后艾滋病流行袭来。 1981 年《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暗示一种新的疾病正在大肆夺去人们的生命。随之而来的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对同性恋无知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悲剧。尽管如此,到 1987 年第一次关于艾滋病毒的疫苗试验开始进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场全球抗击传染病的斗争,剧作家拉里克莱默创办了抗艾滋病激进组织 ACT UP,而第一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AZT 投入使用。
即便如此,科学仍然很难理解这种瘟疫或是开发出一种能预防这种病毒的疫苗。到 20 世纪末,美国有超过 10 万人受到感染。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这些患者的死亡率与现在一样都是 100%。多尔曼了解疫苗,他开始与疫苗学界的其他人讨论是否参与抗击这场瘟疫的战斗。唐·弗朗西斯 (Don Francis) 是一名长期从事疾病研究的人,当时在疾病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工作,也是研究团队的主角之一。为什么不尝试解决艾滋病问题呢?
多尔曼很怀念那段时光。起初的一切努力看起来很混乱。多尔曼把他的疫苗开发团队老班底聚集在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的儿子萨姆隐约有印象。 “我小时候的印象是,有人在受苦,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我的父亲他们觉得自己责任做点什么。”萨姆说。
多尔曼决定试一试。今天,他的名字让人能够想起艾滋病早期的一些故事,以及对疫苗的研究。他的疫情初期的一些故事以及寻找抗病毒疫苗的故事。比如乔恩·科恩(Jon Cohen)的《Shots in the Dark》和帕特里夏·托马斯的《Big Shot》等作品都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从那时起,像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样的新疗法已经使艾滋病毒感染转变为可能与人体共存而不是死亡的东西,至少在发达国家就是如此。直到现在,寻找疫苗的工作仍在继续,十年如一日,乐观情绪和挫败感起起伏伏,潮起潮落。
多尔曼也在努力。但他所做的事推广一种开发疫苗的方法,因为他认为整个科学体系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方法。多尔曼倡导一条大可以称为“古典”的道路。这几乎是反复试验的结果,,可以追溯到天花和狂犬病等疫苗的开发。像早期的疫苗专家一样——詹纳,巴斯德,萨尔克,多尔曼也是一位能够以一种引发免疫反应的方式来指导如何生长,杀死和管理病毒的修复者。如果研究人员不了解潜在的免疫学知识的话,多尔曼就能够起到作用——事实上也经常是这样。
由于艾滋病毒的作用方式——病毒如何感染细胞,感染细胞的种类,病毒如何变异和繁殖——以及疫苗如何被检测和进化,大多数从事艾滋病免疫学的科学家并不认为这样的经典方法能够起作用。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分解和重新排列病毒的特定片段,如嵌入病毒外壳中的糖和蛋白质,并将其与增强剂一起递送。这些来自重组 DNA 和蛋白质技术的方法本身要有更多的假设驱动,似乎也更加合理。最重要是的,这是获得政府机构和制药公司几乎所有研究经费的方法。
完全合理。然而,自从科学家分离出导致艾滋病的病毒以来三十五年间,全球已有三千五百万人在等待疫苗时死于这种疾病。 多尔曼说:“有朝一日我们将充分理解生物学,可以合理设计疫苗,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应该努力从已知方法中提取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多尔曼三十年来一直在坚持重申的观点。但它还没有发生。

图示:现年 80 岁的多尔曼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动对艾滋病毒进行经典疫苗研究。他说:“我们应该努力从已经发明的方法中提取出我们所能提取的东西。”
对于主流科学界来说,多尔曼就像是唐吉柯德,其探索充其量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的研究对象只是由糖蛋白和 RNA 组成的风车。但现年 80 岁的多尔曼并没有放弃。他确信,如果科学界的其他人在几十年前加入他的阵营的话,数百万人的生命就会得到拯救。现在他们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不是科学问题,至少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这是科学文化的问题,是关于研究进程的决策架构。
这并不意味着多尔曼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他会第一个说他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也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没有人知道。不确定。
随便指出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无论是天花、小儿麻痹症还是埃博拉病毒病毒都是如此。不管发病时的症状有多严重,只要痊愈的人就会变得更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表示,在经历各种各样的病毒性疾病后,“绝大多数人会幸存下来。当人们活下来的时候,就是完全消灭病毒的时候。不仅如此,人们在余生中都会对这种病毒免疫。”
人们发现的这种迹象暗示疫苗对这些疾病和其他疾病可能是起作用的。这是一个创造触发器的问题,而这会加速自然界中已有的进程。
在 18 世纪晚期,人们知道得牛痘后不太可能患上天花。而在当时的欧洲,平均每年有超过 40 万人死于天花。牛痘是一种人体免疫系统可以抵抗的病毒,而这种抗体的细胞记录——也就是在免疫系统中创建防御协议——通常也能够免疫天花。这导致科学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故意让一名男孩感染牛痘。当这个男孩后来被发现对天花病毒免疫时,詹纳的方法推广开来,天花导致的死亡人数骤减。牛痘的拉丁文名称是 vaccinia,跟在拉丁文“cow”(牛)的后面,因此詹纳将他的治疗过程命名为“疫苗接种”。
时间跨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当时在美国每年有 16,000 人患上麻痹性脊髓灰质炎,其中大多数是儿童。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 的想法是疫苗实际上并不需要感染某种疾病才能启动人体的免疫系统,他学会了用甲醛杀死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注射进人体。尽管阿尔伯特·萨宾 (Albert Sabin) 等人认为甲醛会缩短免疫期,但这种“灭活病毒”疫苗起效了。

图示:1988 年的多尔曼和他 12 岁的儿子萨姆。
这是 20 世纪风格的经典疫苗学,具有典型的经验主义。这条路并不是平坦笔直的。并不总是平直的。正如科恩在《 Shots in the Dark》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索尔克在儿童身上测试他的疫苗——几乎没有任何许可,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更没有现在研究人员进行实验所获得的食品药监局的批准或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签字。他只是……做了。而这种方法起效了。小儿麻痹症在地球上已经基本消失,而天花也已经不复存在。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奇迹出现了——用在人类身上的有大约 50 种疫苗,而用在其他动物身上的有数百种。存在于人类身上,有数百种为我们生活的非人类动物。实质上,开发所有这些药物的过程几乎都涉及到将病原体置于实验室的每一种工具之下——如何在培养皿中生长,如何杀死或稀释病原体,与病原体一起施用哪些化学品,给多少剂量以及间隔多久。理想情况下, 研究人员最终能够得到一种可以让人体产生免疫力的新组合。这是一个诸如萨姆、多尔曼这样的科技企业家非常认同的产品开发过程。一个经历多次迭代的工程问题。

图示:1985 年,时任 Advanced Genetics Research Institute 公司总裁的多尔曼
但问题在于:传统的疫苗学可能不适用于艾滋病病毒。 福西说:“没有关于某人感染了病毒,真正感染了病毒,然后清除病毒的记录。”同一个人甚至可能会感染两种不同的毒株。
为什么?首先,艾滋病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一种很少会感染人类的病毒。这种狡猾的病毒——富含蛋白质和糖分子的脂肪层包裹着一堆遗传物质——侵入细胞并复制其遗传物质 RNA,将其转化为 DNA,然后再将其插入到宿主细胞的细胞核中,使得病毒 DNA 成为了人的一部分。如今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中断了这一过程——它们阻止病毒 RNA 变成 DNA,或阻止其融合到细胞基因组中,或阻止细胞制造新病毒。但是停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后,病毒又会再次爆发。
也许更重要的是,艾滋病毒攻击的细胞原本是介导对病原体反应的细胞,其中就包括对人体免疫至关重要的 CD4 T 细胞。 CD4 是细胞外部的一种蛋白质,对于人体免疫反应也非常重要;CD4 也是艾滋病附着并用于侵入这些细胞的蛋白质。病毒外壳一种叫做 gp120 的混合糖蛋白像一把钥匙一样附着在 CD4 上,为其他艾滋病蛋白打开了大门,从而让病毒与细胞融合并注入其基因。
这种病毒不仅能够非常快速地复制,而且许多不同毒株也会发生变异。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任何入侵者,但它也学会根据病原体外壳上的特定蛋白质对特定病原体做出反应,如同识别出敌方战斗人员的制服一样。在研究艾滋病病毒时,研究人员了解到这种病毒外壳上的蛋白质会出现变化。艾滋病病毒的糖蛋白每一代都有轻微的变化,这使得病毒可以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检测。换句话说,这种病毒脱下了旧制服,换上了稍有不同的装备,从而避开了免疫系统的监视策略。
经过 35 年的研究,这些细微差别才得以发现。与其他病原体不同,没有任何关于艾滋病病毒有疫苗的迹象。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艾滋病疫苗试验网络首席研究员拉里·科里(Larry Corey)说, “目前我们在 6500 万的自我治愈方面是零。”
但有一个问题在早期就已经很清楚了。当人们开始关注疫苗策略时,他们对于自己能够杀死或完全灭活艾滋病病毒失去了信心——这种信心不仅是对疫苗的必要判断,而且也有对测试者的正确判断。

图示:1987 年首次艾滋病纪念活动在华盛顿特区举行
现在的疫苗测试比索尔克时代受到更多管制,并且需要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当人们报名参加测试时,这些研究对象不知道他们得到的是安慰剂还是药物。由于艾滋病几乎是普遍致命的,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希望能够向测试人员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意外得上这种疾病。 “我们可以真诚地告诉他们,你不会从药物试验中感染艾滋病毒,”AVAC 执行董事米切尔沃伦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从而可以让人们参与到临床试验中来。现在我们还无法用一个完整的灭活疫苗实现这一点。”
即使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员依旧在反思经典疫苗技术的可能性。但艾滋病病毒的复杂性加之研究人员关于人类免疫系统对这种病毒反应的理解不断变化,以及对造成新感染的恐惧都导致他们拒绝这种方法。而基因工程的发展,或者说重组 DNA 技术让研究人员似乎看到了开发艾滋病疫苗的途径,甚至是一种全新的疫苗开发途径。
与多尔曼倡导的经典疫苗开发框架不同,科学家们将利用基因和蛋白质工程技术从头开始开发疫苗,分析艾滋病病毒片段、了解免疫系统如何处理其他病毒,“佐剂”药物促进免疫反应...... 零碎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精致的免疫系统生物技术。
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针对乙型肝炎和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的疫苗都是由此诞生。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它也使科学家能够更多地了解关于病原体和免疫学的知识。它似乎成为了开发艾滋病毒疫苗的最佳途径。

图示:国家广场草坪上铺满了艾滋病纪念展布,1992 年展出了 20000 张展布。
多尔曼是在小儿麻痹症时代长大的,当时这种病毒似乎是不可阻挡的杀手。在帕萨迪纳成长期间,多尔曼看到社区游泳池因此而关闭,电影院因此而关闭。
起初他不打算涉足疫苗行业;多尔曼认为他会成为研究人员和教授。 “但是在我完成癌症协会博士后研究之前,我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说。从事学术研究并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一个年轻的家庭。因此,多尔曼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研发动物疫苗。当时并不是说这个行业绝对赚钱者。正如多尔曼所说,“当时在动物健康领域还没有这样的产品。”多尔曼在学院之外进行科学研究并没有像在今天的风险资本化温室中一样得到尊重。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你离开学术界,感觉都是被迫的,”多尔曼说。但实际上生意真的成功了。这使得他在疫苗学方面显得与众不同:伯特·多尔曼实际上已经制造出了疫苗,而大多数研究艾滋病病毒的人却没有。

图示:美国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与佐治亚州温泉基金会脊髓灰质炎患者进行交谈。
后来多尔曼的生意换了方向。 他卖掉了疫苗公司,并转而开发诊断技术。然后在 1988 年,他写了一份关于研究艾滋病毒的提案,如何制造病毒,净化病毒,杀死病毒,研究如何将其制成疫苗,计算剂量,组合一百种不同的变量,结合临床实验进行不断调整。多尔曼将其发给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他说,给我两年和五百万美元,他就能研制出一种可用于人体实验的疫苗。 “NIH 临床研究部门嘲笑说,”他说, “我反驳说,好吧,我需要四年和一千万美元,但这只会让他们更生气。”(福西表示不记得这个提案或多尔曼。)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疫苗研究的停滞不前,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对相关研究做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承诺,多尔曼仍在努力。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等基金会资助成立了国际艾滋病疫苗联盟(称为 IAVI)。 “那时我向 NIH 写了很多失败的提案,工作人员都很回避,”他说。 “那些年我去拜访 IAVI,拜访盖茨。最终我把感激之情抛在了九霄云外。”所有这些投资者都会说杀死的病毒不可能对抗艾滋病毒。
多曼依旧会争辩。他说,让我们试试看吧。简单地测试这个想法可能会提供有关艾滋病的新知识,以及所谓的人体免疫系统保护相关性,这样一来其他疫苗制造商也会清楚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要寻找什么。多尔曼一直在投石问路。他收到了来自研究人员的信,他们说他的观点可能有道理。他试图在杂志上发表论文,但没有成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0 年。“然后我就放弃了,”多曼说, “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毁了我自己的诊断公司。”

图示:1989 年美国公共卫生机构张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海报。
科学并不是开发艾滋病毒疫苗的唯一难点。整个行业现状也很糟糕。2010 年,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在《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为疫苗缺乏做出了合理解释,但现状听起来让人无奈。他写道,公共资助的科学非常善于提出新知识并传播开来。但这仅仅是研究。但社会将研发的另一半——开发留给了企业。而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利润。
从这个角度来看,疫苗开发的前景并不好。例如,弗朗西斯写道,20 世纪 90 年代 VaxGen 花了 3 亿美元开发艾滋病疫苗,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而 Avirion 单单将一种鼻流感疫苗 Flumist 推向市场就花掉了 3.4 亿美元。 (另一位作者推测,为了开发一种重组减虫登革疫苗,赛诺菲巴斯德花费了 14 亿美元,耗时 24 年时间。)
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许他们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事实上,疫苗生产商也有非政府组织或慈善基金。无论如何,这些激励措施都是颠倒的。即便一个疫苗制造商得到了关于疫苗生产的批复,也很难在公开市场上获得销量。疫苗是预防而不是治疗,只需要一个或几个剂量的药物便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流感疫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图示:1987 年纽约州卫生部发行的艾滋病公共卫生海报
这意味着公司只进行一次销售,而不是让患者终生服药。从需求方面说,许多人很难会为未来可能患上某种疾病而买单。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不太可能为疫苗产品付款。因此对于企业老说,相比于研发疫苗,研发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更具优势。可以这么说:2001 年所有已知疫苗的全部市场体量仅仅与抗胆固醇药物立普妥的市场规模相当。
一些亿万富翁试图通过砸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弗朗西斯的文章承认,来自沃伦巴菲特以及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捐款为疫苗研发注入了数十亿美元,但诸如基金会和基层组织的努力倾向于针对单一疾病的单一疫苗研发,反而会限制广泛有用知识的发展。多尔曼说:“私营组织往往会致力于那些专有性强,可申请专利和有利可图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期望的事情,并希望他们的投资也是如此。我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
事实上他有点儿抨击现状的意味。伯特·多尔曼已经为此努力了三十年。他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老学究。在长时间的电子邮件往来中,你大概可以理解多尔曼为什么不止一次重复,他和其他那些几十年坚持同一件事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所概括的悲剧因一种诱人的可能性而变得更糟:如果他是对的呢,会怎样?今天不再用坐在咖啡店里谈论疫苗。不用花三十年的时间,还有三千五百万人的姓名?
如果他真的是对的呢?

图示: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多尔曼、福西和艾滋病研究人员 Nobuyoshi Shimizu
多尔曼说他对历史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在 2008 年,他恰好阅读了《基督教黑暗史》(Constantine’s Sword),作者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在书中讲述了天主教会与犹太教的关系以及教会做了什么以及没做什么来应对大屠杀。卡罗尔在书中的观点使他感到特别震惊:历史绝非偶然。具体的人会做出具体的选择。
他意识到他必须再试一次。几年之后的 2010 年,经过多年的技术打磨和产品研发后,多尔曼的儿子萨姆决定加入父亲的阵营。萨姆琢磨了一会儿视频,认为这可能会有所作为。 “我当时只是想,也许我可以帮助父亲一点点忙。他写了漂亮的信件和漂亮的论文,他对自己能够影响别人的能力有很大的信心,“萨姆说, “但我想,如果我能带来更多现代化,视觉化的故事,那么它可能会有所帮助。”
所以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 Kill 艾滋病 Now.org。几十年来,多尔曼一直保留着很多疾病专家的证言信,并试图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如今,多尔曼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观点都被萨姆变成了网络视频,阐述着这个问题。
但宣传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
今年,有史以来第一次,研究人员在人类身上测试了一种疫苗,似乎正在对病毒起作用。
像所有正在研发的疫苗一样,其有很多不同的名称。这种疫苗因首次显现效果的地方而被命名为泰国疫苗,也被称之为 RV14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疫苗诞生的历史是经典和假设驱动疫苗学的混合结果。研究人员注意到,长期无进展者出现了控制疾病的所谓细胞反应,所以最好尝试去诱导这些反应。
研究人员还清楚,一种特殊抗体的注入可以防止感染一种在实验室创造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抗体和 t 细胞反应可以保护猴子免受 S - 艾滋病和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的感染。他们随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试验,用艾滋病毒糖蛋白 gp120 做的疫苗没有效果,但它确实暗示了各种可能的免疫特性。

图示:1987 年 6 月 1 日,艾滋病抗议组织“挺身而出”在白宫前示威,要求为艾滋病研究提供更多资金。
因此 RV144 将所有这些都混合在一起——将需要 4 次加强注射的 canarypox 载体疫苗和 2 次加强注射的 gp120 疫苗混合在一起。 2009 年,泰国公共卫生部,泰国大学,NIAID,美国军方和许多其他地方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报告说,RV144 的疗效为 31.2%。也就是说,测试组中受感染的人数比对照组少了约三分之一。
这似乎并不是很多,但它比任何其他艾滋病毒疫苗都做得更好。在南非目前有 5000 多人正在接受新的测试。
另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则使用腺病毒作为载体,同时混合来自几种艾滋病变体的基因和一种具有不同成分组合的加强剂,或者另一种来自艾滋病称之为 gp140 的包膜蛋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它在猴子和人身上显现出一些保护作用。
然而,第三项研究则采用了在经典疫苗学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方法。这些研究人员了解到一种被称为广泛中和抗体的免疫细胞可以防止人体感染艾滋病毒的一种主要毒株。具体而言,研究人员正在使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开发的名为 VRC01 的抗体,将其直接注入男男性行为者和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变性人体内,观察其能否提供保护。顾名思义,它只是许多潜在抗体中的第一个——这是一种“概念证明”,AVAC 的沃伦表示。

图示:2010 年,萨姆·多尔曼 (Sam Dorman) 加入了父亲重启经典疫苗研究的努力。他说:“我认为,如果能带来更现代、更直观的故事,或许会有所帮助。”
多年以来的免疫学研究让科学家能够更快地理解各种结果。今天的疫苗制造商拥有一整套全新的工具,可以让他们从小型测试组中获得结果,并在不间断测试的情况下重新设计配方。 “这就是去风险,”科里说, “你可以进行所有的工程。这很复杂,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概念。“
事实上,长达三十年的工作已经使整个免疫学发生了转变。它看起来更像是产品开发。 IAV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范伯格(Mark Feinberg)说“我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分辨率工具,能够从分子水平上理解抗体和病毒表面,从而认识到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免疫反应。”他表示,早在测试新药物安全性的试验第一阶段,疫苗研究人员就可以了解他们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上。
与此同时,福西仍然表示疫苗即将到来——尽管其可能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包皮环切术,预防性药物和抗体注射结合使用。但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有效地阻止这种流行病。 “我们会接受 55%、60% 的有效疫苗,”他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买账。 “他们正在做不同 RV144 等级的测试,而这只是一种额外的助推器,一种不同的佐剂,”艾滋病.2 发现者之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病毒学家乔·列维(Jay Levy)表示, “我们甚至不知道 RV144 是能否被复制。”他的挫败感是显而易见的,“你正在和一直在抱怨这件事的人谈话。事实上你是被锁定在一个项目中,并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中,所以任何创新都必须与这个方向联系起来。“
就像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一样,艾滋病毒疫苗总是在 10 年之后,并且一直存在。但是所有这些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都再一次激起了那些多年从事疫苗研究的人员的兴奋之情。 “我认为 2018 年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乐观的一年,”沃伦说。
与此同时,也有人试图开发一种艾滋病毒疫苗,其看起来和多尔曼所倡导的方法比较相似。西安大略大学病毒学家康志勇(音译,Chil-Yong Kang)开发的疫苗就处于第一阶段 (基础安全性测试)。
这并不容易。康表示,首先在惯常认知中艾滋病不应生长,监管机构不喜欢某人携带大量艾滋病毒的想法。然后,一旦实验者携带有病毒,康又面临另一个障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FDA 说,如果疫苗中存在单一的活病毒,那就太多了,对吧?”康说,作为试验的前提条件,FDA 告知康必须拿出被彻底杀死的病毒疫苗。
所以康杀死了病毒。他的小组首先对这种病毒进行了基因工程改造,以使其不再感染细胞,但仍然可以复制。然后他们注入了一种称为 Aldrithiol- 2 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标准的病毒杀手。然后他们将有毒的突变病毒暴露于γ辐射以破坏其所有基因。
当康带着处理后的灭活病毒再次回到 FDA 时,“FDA 建议我们应该使用艾滋病毒阳性的个体进行测试,因为人类一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目标是安全,”他说, “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这项研究发布于 2016 年,研究对象仅有 33 名志愿者。在实际上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似乎都能很好地忍受疫苗副作用。 “对于发生的副作用,我们也可以观察免疫反应,”康说,“如果疫苗能够起作用,也应该可以刺激抗体产生,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接种疫苗的人提高了免疫反应,而且广泛中和抗体的水平提高,这使得艾滋病研究人员非常乐观。
康说,他希望今年能够进行二期临床试验——通过改变抗原数量和免疫频率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免疫反应,然后他希望另一组试验能够在艾滋病毒阴性人群中开展。 (康的资金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联邦机构,以及一家名为 Sumagen 的生物技术公司。)
即便对于这种方法,多尔曼仍然持怀疑态度。 “我已经试着向康博士解释,我认为哪些问题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多曼说, “他选择了一种病毒株,这种毒株和相应的细胞系统都很方便。他做了一个克隆程序,因为他有理由认为它可能有用。这种疫苗产生效果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不是对他的批评。这只是承认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做出这种选择,而且有很多这样的选择。”
但是,我说,康的工作不就是接受你的想法的标志吗?你说没有人会资助一种经典方法,但现在是这样的。
“我担心的是,如果它最终失败了,会进一步抹黑这个概念。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他,”多尔曼回答。
我说,他获得支持了。他从两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一家制药公司获得了资金。
多尔曼坚持认为,他支持康志勇,但有很多人都获得过资金并开发出早期的艾滋病疫苗。 “你不能单纯靠自己的想法去开发出一种疫苗,你必须加以反复试验, “他说。 “这是福西们从未消化过的想法。这是一种批评吗?不,他们处于不同的行业,他们的业务也有很大的优势。但他们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疫苗。“
科学——一套方法,而不是体制——仍然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推而广之,它也是人类学习改变世界,创造新事物的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和科学家总是正确的。这些方法是迭代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做的更正确,或者了解到底错在哪里。
他们对艾滋病疫苗的看法肯定不对。 “我们已经为止努力了三十年,依旧一无所获。 RV144 也是这样,”莱文说, “伯特试图获得独立的资助,我认为他仍然可以,但必须来自一些相当有远见的慈善家,因为这种想法无法从基金会获得资金,也不会从政府那里得到。”
多尔曼认为,疫苗界对经典疫苗学的抵抗是一种偏见,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否定了这种想法。 “直到最近,专家还认为地球是平的!正如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等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错误的想法有时很难消除。”他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附了一份 PDF 文件,其中引用了托尔斯泰和辛克莱的话。
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偏见,不如说是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架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写道,科学家们建立了范式,这些理念为研究工作提供信息和指导,直到另一中范式推翻现有的范式。这些范式转变很难预测,几乎不可能进行设计,而且当转变发生时,就会引起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地质学家花了几十年才接受板块构造学的想法。
主导范式早在三十五年前就离开了伯特·多尔曼(Burt Dorman)。现在看来,这种主导范式尚未产生疫苗。多尔曼也从未尝试过他的方法,这无疑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也许,是一场悲剧。(晗冰)